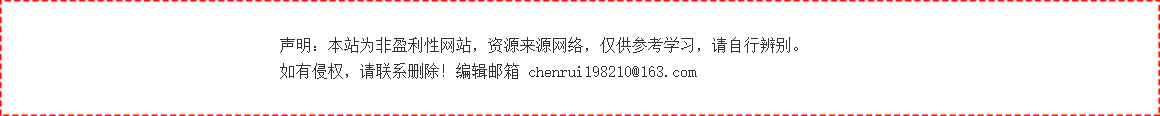像我们这种伪文青,都是怀旧文章过六一,比如我,在这天就想起了一只鸡....哦不好意思。。是一篇关于吃鸡的文章,这么多年都没忘过。到现在,我也想问一句,松鸡跟普通的鸡,吃起来究竟有啥不同呢??
秋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大森林上面,潮湿的风缓缓地吹着。吸饱雨水的树枝垂下来。河水涨到齐了岸。我和猎人划着小船顺流而下。到了河身狭窄的地方,小船突然撞在水面下的树桩上,翻了。食物和打来的野味全给冲走了,我们只好带着猎枪上了岸。
这里离住所还很远。我们俩浑身是水,又累又饿。我冷得发抖,呆呆地望着猎人,希望他有个办法。猎人不声不响,只顾拧他的衣服。“应该生一堆火呀!”我提议,可是从口袋里摸出火柴盒一看,里面竟流出水来。
猎人还是不声不响。他在一棵枞树的窟窿里找到了一些干的苔藓,又拿出一颗子弹,拔下弹头,把苔藓塞进弹壳,塞得紧紧的。他吩咐我:“你去找些干的树枝和树皮来。”
我找来了。他把那颗拔掉弹头的子弹装进枪膛,对着地面开了一枪。从枪口喷出来的苔藓烧着了。他小心地把火吹旺,把树枝和树皮一点儿一点儿加上去,不一会儿,篝火熊熊,烧得很旺。
“你照看火堆。我去打些野味来。”猎人说着,转到树背后就不见了。只听见树林里响了几枪。我还没捡到多少干柴,他已经回来了。几只松鸡挂在他腰上,摇摇晃晃的。
“我们做晚饭吧。”他说。他把火堆移到一边,用刀子在刚才烧火的地上挖了个洞。我把松鸡拔了毛,掏了内脏。猎人又找来几片大树叶,把松鸡裹好,放进洞里,盖上薄薄的一层土,然后在上面又烧起一堆火。
等我们把衣服烘干,松鸡也烧好了,扒开洞,就闻到一股香味。我们俩大吃起来,我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鲜美的东西。
天黑了,风刮过树顶,呼呼地响。
“睡吧。”猎人打了个呵欠说。
我的眼也快要合上了。可是这潮湿冰冷的地面,怎么能睡呢?
猎人带着我折来许多枞树枝。他把两个火堆移开,在烤热的地面上铺上枞树枝,铺了厚厚的一层。热气透上来,暖烘烘的,我们睡得很舒服,跟睡在炕上一个样。
天亮了,我对猎人说:“你真有办法。要不是你,我一定要吃苦头了。”
猎人微笑着说:“大森林里,你不能像个客人,得像个主人。只要肯动脑筋,一切东西都可以拿来用。”
《大森林的主人》

金秋十月,故乡的柚子熟了。
旅居海外的伯父带着十五岁的女儿从遥远的南美洲回到了浮云镇。
第二天一大早,堂妹就嚷着要我陪她去买柚子。
“去,我也去”。伯父笑着说,“她没见过柚子,我也四十年没吃过柚子了,我们都得了思柚病。”
正是柚子上市的旺季,一筐筐黄澄澄的柚子摆在街道两旁,卖的人在吆喝:
“卖柚子,好甜的柚子!”
“先尝后买,不甜不要钱!”
我们东瞧瞧,西看看,不知买谁的好。
往前走,来到一个卖柚子的小姑娘跟前,她大约和堂妹一样年纪。红红的脸蛋上印着两个浅浅的酒窝,胸前,别着一枚中学校徽。她安静地坐在那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出神地盯着打开的书,看样子她早已忘了自己是卖柚子的了。
“多少钱一个?”伯父指着她那筐又大又黄的柚子问。
“一毛”。
“这么便宜”。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卖柚子,她说自己家的,卖便宜点”。
“这是什么柚子?” 伯父又问。
“这叫棉花柚,个儿大,其实里面的肉不多。”姑娘合上书,郑重其事的说。
伯父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接着问:
“甜吗?”
小姑娘害羞地摇摇头:“有点苦。”
伯父有些激动:“好,我买十个!”
“十个?”小姑娘睁大眼睛望着老人,仿佛没有听清他的话。
“是十个。”
“您要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吗?”
“是的,我住在圣地亚哥,你学过地理吧,智利,在南美洲,太平洋彼岸,离这儿有一万多里呢。”
“少买一点吧。”
“为什么?”
“这种柚子确实不大好吃,苦味很浓,人们都不喜欢。”小姑娘站起身来,接着说:“再说,你好不容易从国外回来,要把家乡的柚子带到外国去,应该买点好的,甜的。”
“你说得很对。”伯父拉着小姑娘的手,连声说:“孩子,凭着你这颗善良的心,诚实的心,苦柚子也会变甜的。”
小姑娘腼腆地笑了。
“这筐柚子,我全买下!” 伯父说着更加激动了。
我和堂妹打开旅行袋,把一筐柚子装了进去。
堂妹付完钱,伯父把一张崭新的一百元钞票塞到小姑娘手里说:“祝你幸福,好孩子!”
小姑娘说什么也不肯要,把一百元还给伯父,提起空筐,飞快地消失在人流中。
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海外归客,同时啧啧称赞。
秋阳高照,映红了美丽的山乡小镇。回家的路上,我和堂妹提着沉甸甸的旅行袋,一边走,一边听着伯父意味深长的赞叹:在这个世界上,金钱可以买到山珍海味,可以买到金银珠宝,就是买不到高尚的灵魂哪!
苦柚,那一袋苦柚,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苦柚》

多年以前,我曾冒着霏霏细雨,乘独木舟过江.上岸,走进大峡谷,天已经黑了.吃罢饭,边防军连长有些神秘地对我说:"不久会有可爱的小朋友给你送礼物."送礼物,谁呢?我想一定是哪个孩子.
边防哨所从来没有上锁插门的习惯.敞着门,我睡得甜极了.第二天醒来,蒙眬中听到一点响动,睁眼一看,见桌子上多了一小把香蕉.忙起身追出去,见是一只毛色鲜亮的猴子,回头看了我一眼,还点点头,转过屋角,闪进丛林,蹿到树上消失了.
这就是雪猴,与普通猴子的最大区别是躯体较为高大,鼻孔高傲地翻向天空.它们是边防军人的好朋友,见了穿军装的人就显得非常高兴.如果来了新客人,就会热情地送上一点森林中的礼物.
我的窗前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这就是雪猴的乐园.几天下来我发现,雪猴和边防军人相处得是那么友好.
清早,嘹亮的号音伴来晨光,军人出操了.树林里,雪猴也按号音起身,攀枝欢跳,飞身跃林,开始做"早操".军人到哨所旁边溪水畔洗脸刷牙,猴儿也一齐拥到水边,用爪子捧水抹抹脸,把脚趾伸到嘴里掏掏,那神态像是很认真.军人在场上操练,猴儿就蹲在枝头观赏,有时还咧嘴龇牙地狂叫,仿佛为军人鼓劲叫好.兴致来了,它们还会跳到地上,在一旁摹仿.一次,一个新战士从单杠上摔下来,首先奔上去的竟是猴儿.它们把那个战士围得严严实实,又蹦又跳,用它们特有的方式表示关切和同情.战士们上课,它们也会不远不近地学着战士们席地而坐,凝神听讲,只有身上不舒服时才用爪子搔一搔.
一次,友人陪我到山下寨子里去采访.归来时,我们在一片青草地上休息,聊天.突然,猴王带领它的部下把我们团团围住.它们有的把头垂得很低,有的用爪子紧捂朝天鼻,有的甚至把鼻孔抵在肚子上;它们左蹦右跳,扯着嗓子乱叫.我正大惑不解时,友人忙拉我快走.他说这里气候变化莫测,常常一个时辰就可以出现阴晴雨雪、冰雹风霜多种天气.雪猴对这里的气候最敏感,刚才它们是向我们预报有大雨,催我们快走.果然,我们刚回到哨所,就下起暴雨,雨中还夹着冰雹.
离开大峡谷哨所时,我才更加明白,为什么有的战士服役期满,不只与部队难以割舍,还舍不得那些雪猴.

《雪猴》

九岁的凡卡·茹科夫,三个月前给送到鞋匠阿里亚希涅那儿做学徒。圣诞节前夜,他没躺下睡觉。他等老板、老板娘和几个伙计到教堂做礼拜去了,就从老板的立柜里拿出一小瓶墨水,一支笔尖生了锈的钢笔,摩平一张揉皱了的白纸,写起信来。
在写第一个字母以前,他担心地朝门口和窗户看了几眼,又斜着眼看了一下那个昏暗的神像,神像两边是两排架子,架子上摆满了楦头①。他叹了一口气,跪在作台前边,把那张纸铺在作台上。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他写道,“我在给您写信。祝您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求上帝保佑您。我没爹没娘,只有您一个亲人了。”
凡卡朝黑糊糊的窗户看看,玻璃窗上映出蜡烛的模糊的影子;他想象着他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里奇,好像爷爷就在眼前。爷爷是日发略维夫老爷家里的守夜人。他是个非常有趣的瘦小的老头儿,65岁,老是笑咪咪地眨着眼睛。白天,他总是在大厨房里睡觉。到晚上,他就穿上宽大的羊皮袄,敲着梆子,在别墅的周围走来走去。老母狗卡希旦卡和公狗泥鳅低着头跟在他后头。泥鳅是一条非常听话非常讨人喜欢的狗。它身子是黑的,像黄鼠狼那样长长的,所以叫它泥鳅。
现在,爷爷一定站在大门口,眯缝着眼睛看那乡村教堂的红亮的窗户。他一定在跺着穿着高筒毡靴的脚,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缩成一团,耸着肩膀……
天气真好,晴朗,一丝风也没有,干冷干冷的。那是没有月亮的夜晚,可是整个村子——白房顶啦,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的烟啦,披着浓霜一身银白的树木啦,雪堆啦,全看得见。天空撒满了快活地眨着眼睛的星星,天河显得很清楚,仿佛为了过节,有人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
凡卡叹了口气,蘸了蘸笔尖,接着写下去。
“昨天晚上我挨了一顿毒打,因为我给他们的小崽子摇摇篮的时候,不知不觉睡着了。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里,拿皮带揍了我一顿。这个礼拜,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弄起,她就捞起那条青鱼,拿鱼嘴直戳我的脸。伙计们捉弄我,他们打发我上酒店去打酒。吃的呢,简直没有。早晨吃一点儿面包,午饭是稀粥,晚上又是一点儿面包;至于菜啦,茶啦,只有老板自己才大吃大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崽子一哭,我就别想睡觉,只好摇那个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吧,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回到我们村子里去吧!我再也受不住了!……我给您跪下了,我会永远为您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要不,我就要死了!……”
凡卡撇撇嘴,拿脏手背揉揉眼睛,抽噎了一下。
“我会替您搓烟叶,”他继续写道,“我会为您祷告上帝。要是我做错了事,您就结结实实地打我一顿好了。要是您怕我找不着活儿,我可以去求那位管家的,看在上帝面上,让我擦皮鞋;要不,我去求菲吉卡答应我帮他放羊。亲爱的爷爷,我再也受不住了,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原想跑回我们村子去,可是我没有鞋,又怕冷。等我长大了,我会照顾您,谁也不敢来欺负您。
“讲到莫斯科,这是个大城市,房子全是老爷们的,有很多马,没有羊,狗一点儿也不凶。圣诞节,这里的小孩子并不举着星星灯走来走去,教堂里的唱诗台不准人随便上去唱诗。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跟钓竿钓丝一块出卖的钓钩,能钓各种各样的鱼,很贵。有一种甚至钓得起一普特②重的大鲇鱼呢。我还看见有些铺子卖各种枪,有一种跟我们老板的枪一样,我想一杆枪要卖一百个卢布吧。肉店里有山鹬啊,鹧鸪啊,野兔啊……可是那些东西哪儿打来的,店里的伙计不肯说。
“亲爱的爷爷,老爷在圣诞树上挂上糖果的时候,请您摘一颗金胡桃,藏在我的绿匣子里头。”
凡卡伤心地叹口气,又呆呆地望着窗口。他想起到树林里去砍圣诞树的总是爷爷,爷爷总是带着他去。多么快乐的日子啊!冻了的山林喳喳地响,爷爷冷得吭吭地咳,他也跟着吭吭地咳……要砍圣诞树了,爷爷先抽一斗烟,再吸一阵子鼻烟,还跟冻僵的小凡卡逗笑一会儿……许多小枞树披着浓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着看哪一棵该死。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只野兔来,箭一样的窜过雪堆。爷爷不由得叫起来,“逮住它,逮住它,逮住它!嘿,短尾巴鬼!”
爷爷把砍下来的树拖回老爷家里,大家就动手打扮那棵树。
“快来吧,亲爱的爷爷,”凡卡接着写道,“我求您看在基督的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的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又孤零零的,难受得没法说。我老是哭。有一天,老板那楦头打我的脑袋,我昏倒了,好容易才醒过来。我的生活没有指望了,连狗都不如!……我问候阿辽娜,问候独眼的艾果尔,问候马车夫。别让旁人拿我的小风琴。您的孙子伊凡·茹科夫。亲爱的爷爷,来吧!”
凡卡把那张写满字的纸折成四折,装进一个信封里,那个信封是前一天晚上花了一个戈比买的。他想了一想,蘸一蘸墨水,写上地址。
“乡下 爷爷收”
然后他抓抓脑袋,再想一想,添上几个字。
“康司坦丁·玛卡里奇”
他很满意没人打搅他写信,就戴上帽子,连破皮袄都没披,只穿着衬衫,跑到街上去了……前一天晚上他问过肉店的伙计,伙计告诉他,信应该丢在邮筒里,从那儿用邮车分送到各地去。邮车上还套着三匹马,响着铃铛,坐着醉醺醺的邮差。凡卡跑到第一个邮筒那儿,把他那宝贵的信塞了进去。
过了一个钟头,他怀着甜蜜的希望睡熟了。他在梦里看见一铺暖炕,炕上坐着他的爷爷,耷拉着两条腿,正在念他的信……泥鳅在炕边走来走去,摇着尾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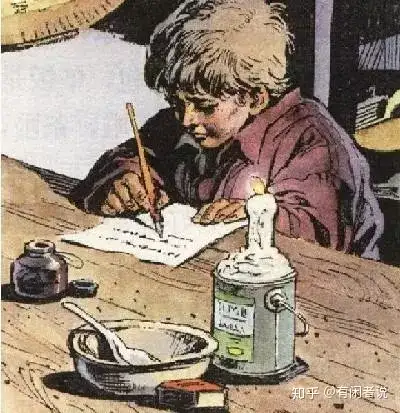
《凡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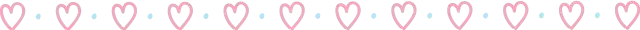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头垂下几根绳子,挂着沉甸甸的物品。登山的时候,他们一只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只胳膊垂着,伴随着步子有节奏地一甩一甩,保持身体平衡。他们的路线是折尺形的--先从台阶的左侧起步,斜行向上,登上七八级台阶,就到了台的右侧;便转过身子,反方向斜行,到了左侧再转回来,每次转身,扁担换一次肩。他们这样曲折向上登,才能使挂在扁担前头的东西不碰在台阶上,还可以省些力气。担了重物,如果照一般登山的人那样直上直下,膝头是受不住的。但是路线曲折,就会使路线加长。挑山工登一次山,走的路程大约比游人多一倍。
奇怪的是挑山工的速度并不比游人慢,你轻快地从他们身边越过,以为把他们甩在后边很远了。你在什么地方饱览壮丽的山色,或者在道边诵读凿在石壁上的古人的题句,或者在喧闹的溪流边洗脸洗脚,他们就会不声不响地从你身旁走过,悄悄地走到你的前头去了。等你发现,你会大吃一惊,以为他们是像仙人那样腾云驾雾赶上来的。
有一次,我同几个画友去泰山写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山下买登山用的青竹杖,遇到一个挑山工,矮个子,脸儿黑生生的,眉毛很浓,大约四十来岁,敞开的白土布褂子中间露出鲜红的背心。他扁担一头拴着几张木凳子,另一头捆着五六个青皮西瓜。我们很快就越过了他。到了回马岭那条陡直的山道前,我们累了,舒开身子躺在一块被山风吹得干干净净的大石头上歇歇脚。我们发现那个挑山工就坐在对面的草茵上抽烟。随后,我们跟他差不多同时起程,很快就把他甩在后边了,直到看不见他。我们爬上半山的五松亭,看见在那株姿态奇特的古松下整理挑儿的正是他,褂子脱掉了,光穿着红背心,现出健美的黑黝黝的肌肉。我很惊异,走过去跟他攀谈起来,这个山民倒不拘束,挺爱说话。他告诉我,他家住在山脚下,天天挑货上山,干了近二十年,一年四季,一天一个来回。他说:“你看我个子小吗?干挑山工的,给扁担压得长不高,都是又矮又粗的。像您这样的高个儿干不了这种活儿,走起路晃悠!”他浓眉一抬,裂开嘴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山民们喝泉水,牙齿都很白。
谈话更随便些了,我把心中那个不解之谜说了出来:“我看你们走得很慢,怎么反而常常跑到我们前头去了呢?你们有什么近道吗?”
他听了,黑生生的脸上显出一丝得意的神色。他想了想说:“我们哪里有近道,还不和你们是一条道?你们走得快,可是你们在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停下来呗!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不像你们那么随便,高兴怎么就怎么。一步踩不实不行,停停住住更不行。那样,两天也到不了山顶。就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边去了。你看,是不是这个理?”
我心悦诚服地点着头,感到这山民的几句朴素的话,似乎包蕴着意味深长的哲理。我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他就担起挑儿起程了。在前边的山道上,我们又几次超过了他;但是总在我们留连山色的时候,他又悄悄地超过了我们。在极顶的小卖部门前,我们又碰见了他,他已经在那里交货了。他憨厚地对我们点头一笑,好像在说;“瞧,我可又跑到你们前头来了!”
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的重物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
《挑山工》

早上,白茫茫的一片大雾.
远处的塔、小山都望不见了.
近处的田野、树林像隔着一层纱,模模糊糊看不清.
太阳像个红球,慢慢地升起来,发出淡淡的光,一点儿也不耀眼.
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人们正在园子里忙着收白菜.
雾慢慢地散了,太阳射出光芒来.
远处的塔、小山都望得见了.近处的田野、树林也看得清了.
柿子树上挂着许多大柿子,像一个一个的红灯笼.
树林里落了厚厚的一层黄叶.只有松树、柏树不怕冷,还是那么绿.

《初冬》

xià xuě la xià xuě la
下 雪 啦,下 雪 啦!xuě dì lǐ lái le yì qún xiǎo huà jiā
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xiǎo jī huà zhú yè xiǎo gǒu huà méi huā
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xiǎo yā huà fēng yè xiǎo mǎ huà yuè yá
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bú yòng yán liào bú yòng bǐ
不 用 颜 料 不 用 笔,jǐ bù jiù chéng yì fú huà
几 步 就 成 一 幅 画。qīng wā wèi shén me méi cān jiā
青 蛙 为 什 么 没 参 加?tā zài dòng lǐ shuì zháo la
他 在 洞 里 睡 着 啦。
《雪地里的小画家》

到位于沙漠地带的叙利亚去旅行,最不能忍受的,是它气候的干燥与闷热。喝下去的水,顷刻间便化成成串的汗,从额上淌下。
因为这样,叙利亚境内,不论大街小巷,不论白天晚上,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卖水人。他们卖的,不是糖浆冰水,而是新鲜的水果汁。最常见的,有橙水、柠檬水和萝卜水。
这些新鲜果汁,价格便宜得叫人难以相信。比方说:“一杯田 4只鲜橙榨出来的果汁,才卖新币 7毛钱,一杯以 5条萝卜压成的萝卜水,才收新币9毛钱。据当地人告诉我:这些都是叙利亚盛产的水果,因为生产得多,价格也就贱了。
令我念念难忘的,倒不是这些又便宜又好喝的水果汁,而是那些卖水人。
为了吸引顾客,叙利亚的卖水人都出尽奇招地来装饰他们的摊位。记得有位卖橙水的,把浑圆的橙堆得好像一座小山一样高,“橙山”上面,满满地插着制作精巧的塑胶花,远远看去,五彩缤纷,橙与花相互争艳。另有位卖萝卜水的,把他又肥又大的事卜叠成一个奇特的图案,惹人驻足而现;这一观,当然便得“破财而欢”了。
最最可爱的,是一些吹笛子的卖水人。他们或站在购物中心,或站在马路旁边,身上挂着一个形似葫芦的巨型铝制水壶,手执笛子,放在嘴边,“咿咿唔唔”地吹出一支又一支幽幽怨怨的曲子。当你经过他身边时,他会用眼睛向你说话:“来吧,来吧,这么热的天气,来喝一杯水吧!”试问,你能抗拒这样的诱惑吗?浸浴在笛子柔美的声音里,喝着从错壶里倒出来的冰冷的酸柑水,你会觉得,整颗。心都凉了起来。喝完以后,把林子递还给他时,你会不由自主地说:“再来一杯。”
卖水人浓厚的人情味,也叫人感动莫名。离我所下榻的旅舍不远处,有一摊卖柠檬水的,摊主是个脸上稚气尚未脱尽的年轻人。他卖的柠檬水,一杯4毛钱,够酸又够浓,确是解渴妙品。早晚经过那儿时,我总要停下来喝上两大杯,一天两趟,4杯,加上外子的,总共8杯。喝到第三天时,他竟对我问说:
“你们晚上喝的,不必付钱。反正,我也要收摊了!”
听了这话,我恍惚间以为错误地闯入了“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了;但定睛一看,站在眼前的,却只是现代的一位卖水人——叙利亚一位笑口常开的卖水人……

尤金——《叙利亚的卖水人》

xiǎo xiǎo zhú pái huà zhōnɡ yóu
小 小 竹 排 画 中 游
xiǎo zhú pái, shùn shuǐ liú,
小 竹 排, 顺 水 流,
niǎo er chànɡ yú er yóu.
鸟 儿 唱, 鱼 儿 游。
liǎnɡ àn shù mù mì,
两 岸 树 木 密,
hé miáo lǜ yóu yóu.
禾 苗 绿 油 油。
jiānɡ nán yú mǐ xiānɡ,
江 南 鱼 米 乡,
xiǎo xiǎo zhú pái huà zhōnɡ yóu
小 小 竹 排 画 中 游。

《小小竹排画中游》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山村咏怀》